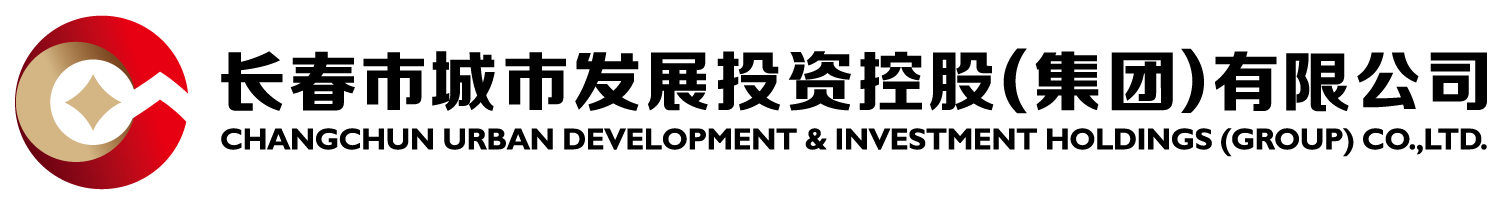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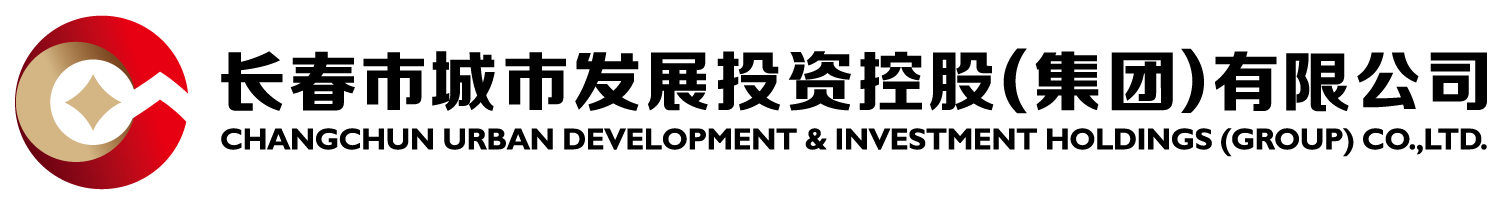

(34) 我心中的共產(chǎn)黨員
華夏智城 許治黎
“從有著古老歷史的中州,傳來了青年的聲音,仿佛預(yù)告這古國將要復(fù)活.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魯迅先生贊共產(chǎn)黨
“在你心中,共產(chǎn)黨員應(yīng)該是什么樣子?”
黨課上,老師的提問讓我一時(shí)錯(cuò)愕,作為一名入黨積極分子,我甚至還沒有體驗(yàn)過“共產(chǎn)黨員”的滋味,更無從談起總結(jié)共產(chǎn)黨員的光輝形象了。無奈地環(huán)視四周,靜悄悄一片,原來不只我一個(gè)人沒有主意。
那,你們身邊有沒有令人尊敬的優(yōu)秀共產(chǎn)黨員?說一說他們的光榮事跡。”
老師不死心,繼續(xù)發(fā)問。一說到具體事例,同學(xué)們像是打開了話匣子,七嘴八舌地鬧將起來。我笑著看向窗外,正迎上滿目的蔥郁——這個(gè)季節(jié)的松樹更加綠了,一籟籟聚在一起,像極了田間新生的麥浪。新生?想到這兒,我突然憶起,前年調(diào)皮的師弟失手將草坪點(diǎn)燃,熊熊烈火將幾棵松樹攔腰燒斷,環(huán)衛(wèi)大叔事后看著“火災(zāi)現(xiàn)場”,不斷感嘆:“可惜!可惜!”。誰知一個(gè)冬天過后,燒斷的樹干上竟奇跡般地發(fā)出了新芽,松樹又活了!環(huán)衛(wèi)大叔不住高喊:“這松樹原也是野火燒不盡啊!”
可不是嗎?整個(gè)校園的綠植,只有它不用特殊關(guān)照就能安然過冬,平日里更是略施雨露便能時(shí)刻茁壯,不嬌貴、不畏難、不服輸、不怕死,錚錚鐵骨卻讓人忍不住親近,傲霜斗雪也能四季常青。這讓我想起我的母親——那個(gè)時(shí)刻將責(zé)任與堅(jiān)守記在心間的共產(chǎn)黨員。
母親生在70年代,只有小學(xué)文化的外公感性地用“江海松濤”給他的四個(gè)孩子命名,母親叫曹振松,是家里唯一的女孩。那個(gè)年代,女孩的命運(yùn)大多相似,母親自然也未能免俗。外公守著公有的飯店,卻養(yǎng)不活四個(gè)兒女,廉潔二字他不認(rèn)得,卻用一輩子貫徹。為了讓三個(gè)哥哥讀書,17歲的母親主動(dòng)輟學(xué),在城里一家化肥廠做工人。半緣時(shí)代,半是家教,拼搏成了她回應(yīng)艱苦生活的唯一態(tài)度。因著她的努力,22歲母親便當(dāng)上車間主任,并順利加入黨組織。母親成為黨員了!這對(duì)沒上過大學(xué)的她來說,是無上的榮光和最值得炫耀的資本,聽父親說,母親把配發(fā)的黨徽細(xì)細(xì)端詳不忍放下,時(shí)刻佩戴,就連結(jié)婚當(dāng)日的喜服上也不肯遺漏。對(duì)于這份榮耀,她有著特殊的執(zhí)拗。
松樹的堅(jiān)韌是霜打的,英雄的風(fēng)采是血染的。
化工廠大小事故不斷,安全生產(chǎn)在彼時(shí)的小縣城還只是一句漂亮話。母親在一次作業(yè)中,恰值遇建廠以來最嚴(yán)重的一次氨氣泄漏,工人們驚慌逃離,形勢(shì)嚴(yán)峻不堪,母親的同事拉住她趕忙往門外跑,跑了一段路后,才反應(yīng)過來的母親迅速折返回去,消失在一片濃霧中。原來,嚴(yán)重的氨泄漏極易導(dǎo)致爆炸,她跑回去,是為了趕在爆炸前擰緊氨氣閥門,制止可能發(fā)生的更大的損失和傷亡。可是,閥門處的濃重氨氣毒性幾乎是致命的。濃氨散去,人們?cè)诎睔忾y旁發(fā)現(xiàn)了奄奄一息的母親,閥門擰緊了,母親卻倒下了。經(jīng)過一個(gè)月反復(fù)的搶救與掙扎,母親總算是從生死線上撿回一條命。可是經(jīng)此一役,她的雙肺有了難以愈合嚴(yán)重?fù)p傷,終生都要靠吸氧維持呼吸,兩室心房因過度損耗也泵血困難,隨時(shí)都有停跳的風(fēng)險(xiǎn),每五秒一次的咳痰成了她生命新的節(jié)奏,雙手雙腳的靜脈曲張點(diǎn)綴著她日后的艱難生活,吊水打針成了家常便飯,成把吃藥就是生活常態(tài)……
“我就不信你不后悔!”
說出這句我自以為擲地有聲地話,挑釁般地等待母親回答。我曾那么恨她,恨她強(qiáng)出風(fēng)頭,恨她不自量力,恨她沒能給我完整的母愛……“沒啥后悔的”,母親安靜地坐在窗前,一邊小心地摩挲著她這輩子最為珍視的榮耀——黨徽,一邊緩緩回應(yīng)我的挑釁。“最起碼廠子沒爆炸,幾億的資產(chǎn)保住了,最起碼廠里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跟你一樣,”說到這里,她蹙眉,一字一頓地繼續(xù)道,“跟你一樣有一個(gè)不健全的媽。”她大抵是說不出諸如奉獻(xiàn)、愛崗、愛國、愛黨這種她認(rèn)為的“文化詞”的。“可為什么?為什么是你?”覺察到我的忿懣,她小心將黨徽章收在盒里,上前拉我的手,一時(shí)無言,世界靜默,只余我不辯是非的抽泣。她的執(zhí)著讓我愈發(fā)恨她,也愈發(fā)心疼她。在世的十年,她飽嘗不曾想見的凄風(fēng)冷雨,從健康跌至羸弱的巨大反差,一下老了十歲的難以接受,無法正常生活的巨大折磨,不被親人理解的剜心煎熬,這種種苦難,個(gè)個(gè)都要她親口咽下。無法摘除的氧氣管和常年趴在手背的靜脈針既是她所有生命力的保障,又是扣住她活力的一張巨網(wǎng),讓她逃無可逃……面對(duì)生命的斑駁,她卻像一棵青松,淡然堅(jiān)守,鏗鏘負(fù)責(zé),從不低頭,從不叫苦,從不后悔,從不服輸,努力“扮演”著一個(gè)愛崗敬業(yè)好職工,一個(gè)伏首奉獻(xiàn)的優(yōu)秀共產(chǎn)黨員,直至生命盡頭。
而今,每當(dāng)我從黨史書上讀到中國共產(chǎn)黨100余年的風(fēng)云激蕩,無數(shù)次的生死悠關(guān),令人欣慰的凱歌飄揚(yáng)和舍生忘死的黨員事跡,眼前總浮現(xiàn)出母親消失在氨氣里的決然和擦拭黨徽的安詳形象,耳畔不斷響起陳毅先生贊美共產(chǎn)黨員的詩句:“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shí)……”
這激昂使我從回憶中驚醒,驚覺回憶的淚水己打濕面前的《中國共產(chǎn)黨章程》,低頭擦拭,醒目的入黨誓詞直逼我眼:
“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擁護(hù)黨的綱領(lǐng),遵守黨的章程, 履行黨員義務(wù),執(zhí)行黨的決定, 嚴(yán)守黨的紀(jì)律,保守黨的秘密,對(duì)黨忠誠,積極工作, 為共產(chǎn)主義奮斗終身,隨時(shí)準(zhǔn)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淚眼婆娑中,我好像突然理解了作為共產(chǎn)黨員的曹振松。